沈卫荣谈“想象西藏”:不要将自己的愿望和期待投射给西藏
作为一名藏学研究者,清华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所的沈卫荣教授对于“想象西藏”这个问题已有二十多年的关注,其著作《想象西藏:跨文化视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密教》就专门研究这一问题。2016年11月19日,《文化纵横》杂志社协同国礼(北京)艺术品有限公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沈卫荣教授来到三联韬奋书店,与听众们探讨东西方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想象”问题。

对西藏的想象反映出想象者的不同文化与社会状况
1990年代留学期间沈卫荣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西方人比他更关注西藏。一方面他感受到西方对西藏的热情;但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西方人关心的西藏跟他所研究、走访的西藏并不一样。他发现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对西藏都知之甚少,也没有足够的耐心去了解一个现实的西藏,对西藏的理解带有普遍的问题。他们关注的仅仅是是一个“虚幻的”和“想象的”西藏。
沈卫荣指出,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揭示的,“想象”对于人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学术研究中,过分的想象或者对被“想象”出来的“真实”不加区别的接受会带来许多问题。大量的“历史真实”是被建构起来的。从阐释学的角度看来,人的认知是有局限的,难以在既有的认知体系中解释一个全然陌生的事物。
意大利符号学问家安伯托·埃柯曾在《从马可·波罗到莱布尼兹——跨文化误解的故事》(From Marco Polo to Leibniz: Stories of Inter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s)一文中指出,人对新事物的理解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都存在“背景书”(Background Books),是一种在所在文化圈所形成的认知,会影响到我们跨文化的理解。许多历史学家都在讨论马可波罗是否真正到过中国,因为他的游记中并没有描写中国人喝茶、用筷子等典型特征。埃柯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当时欧洲读者所期待的东西并不在此。马可波罗的“背景书”让他“发现”了许多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比如东方强大的基督教王国:“约翰长老的王国”(The Kingdom of Prester John)。而这仅仅是中世纪德意志传教士的创造,使得西方人普遍相信它的存在。马可波罗在中国“发现”大量这个王国的“遗迹”。因此可见马可波罗也逃脱不了“背景书”的制约。
沈卫荣指出“想象西藏”是一个国际性的工程,东西方对西藏的想象五花八门,在这些叙述中反映出了想象者的不同文化与社会状况。这种想象的出现首先跟西藏地理的特殊性有关。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西藏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1980年代前只有非常少的西方人到过西藏,任何一个去过西藏的人都有非常特别的经验,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其次西藏文化的独特性,也为想象提供了可能性。但现在地理因素已经不再是人们前往西藏的障碍,交通的改善并没有使对西藏的想象停止,今天想象甚至更加离奇与精致。许多人相信在西藏可以找到灵魂的安宁、精神的解脱或是期待的爱情;所谓仓央嘉措情诗的流行,同样是想象西藏的典型例证。
今天西藏依然在当代东西方人的精神生活中发挥作用,尤其是近年来藏传佛教在中国大陆的影响不断扩大,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对西藏有更多的了解。我们把自己的情感追求甚至恐惧都投射到西藏,从而建构一个“虚幻”的西藏,试图解决自身的问题。
西方想象中的“香格里拉”:对西藏的神话和妖魔化
之后沈卫荣讲述了西方如何是如想象西藏的,他的论述首先从“香格里拉(Shangri-La)”开始。在他看来,香格里拉是“充满帝国主义腐臭”的地方。“香格里拉”来自于1933年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是一个被创作出来的带有殖民主义气息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本身成为西方对殖民时代的怀旧,成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代名词,并不是他们所描述的东方人的圣地。可以说香格里拉是二十世纪欧洲人对东方和东方传统文化的幻想。是西方人创造的一个精神家园。而1990年代中甸县改名“香格里拉”则坐实了这个名称,是一种典型的内部东方主义(Inner Orientalism)。
沈卫荣指出,西方人的西藏想象一方面是神话化,另一方面则是妖魔化。前者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开始,在公元前五世纪在其所著的《历史》中,出现有关西藏的记载,即蚂蚁淘金的传说。而这种传说在西藏本土的传说中也有记载,这大概也是西方人认为西藏遍地是黄金的由来。之后公元一世纪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地理》中不但提到西藏,而且还提到以一座铜色的山。铜色山是藏族人民心中的一座圣山,是藏传佛教大师莲花生隐居之所。可以说历史与传说的杂糅委实匪夷所思。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西方大部分对西藏的印象实际上是妖魔化与色情化。这种印象从马可波罗开始,并且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西方人曾认为西藏是一个天主教的王国,最早到达西藏的西方人,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安东尼奥·德尔·安德拉德(António de Andrade)创作了一本《重新发现大契丹或西藏》。有意思的是,他明明是第一个到达西藏的欧洲人,却说他“重新发现”了西藏,因为他发现西藏早已是天主教王国。到了启蒙时代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高度评价东方文化,但西藏仍被当做一个专制、愚昧、非理性的地域被批判。黑格尔还专门批评西藏活佛转世制度,直到晚近大多数西方人认为这种制度是一种欺骗百姓的政治伎俩。进入殖民主义时代,整个东方都成了西方侵略的目标,它自然应该是愚昧落后的,需要西方的“拯救”,西藏也不例外。无论是西方的传教士还是维多利亚时期东方学家们都对藏传佛教表现出诋毁和不屑,认为藏传佛教根本不配叫做佛教,只能被称为“喇嘛教”。
这种妖魔化的风潮一直到七八十年代依然存在,但同时出现了神话化西藏的过程。西方曾认为远在西方文明的古典时代,西藏与西方就有联系,许多古老的哲学观念在西方永远地丢失了,但它们却在西藏保存下来。相信这一说法的在西方不乏其人,希特勒也曾派出以歇斐博士为首的考察团到西藏寻访雅利安人种的来源。德国慕尼黑国家图书馆中保存有希特勒和当时西藏摄政王热振活佛的往来信件。现代西藏学的诞生也与这种观念有关,一名叫乔玛的匈牙利人抱着寻找匈牙利人之根的初衷来到西藏,学习藏文研究西藏历史文化并创作了第一部藏英字典,成为了世界藏学之父。
对西方神话化西藏影响最大的是神智学(Theosophy),创始人是海伦娜·布拉瓦茨基(Madam Blavatsky),她自称在西藏札什伦布寺附近跟随喇嘛学习密法,找到了开启神智的钥匙,并来到纽约创立神智学会。她宣称要找回已经丢失的神的智慧,建立起一种科学的宗教以对抗科学和进化论。这与西方反对现代化的观点不谋而合,很快风行一时并笼络大批信徒,其中包括像卡尔·荣格、铃木大作这样的名人,被称为中国藏学之父的于道泉先生也是神智学的追随者。
将西藏的神话化推进到一个新高度的是《西藏死亡书》的出版。其作者伊文思·温慈也是神智学的信徒,他将藏传佛教宁玛派的一本密法仪轨翻译成英文,即《西藏死亡书》。1960年代美国嬉皮士运动中有重要影响力的心理学家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将《西藏死亡书》改写成如何使用迷幻剂的指南,认为书中描写的死后世界就跟服用迷幻药后所看到的景象一样,因此服用迷幻药同样可以克服超越死亡,由此该书在西方产生重大影响。与嬉皮士运动紧密相联的是“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是从欧美玄学传统和六十年代的“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中滋生的一种异端宗教、东方哲学和神秘心理现象的混合体。新时代运动大量引进东方传统,特别是东方神秘主义。藏传佛教也被被引入并被神秘化、神话化。激进的密教受到青睐,它为以暴力、毒品和滥交为标志的六十年代经验赋予精神上的和政治上的意义,为其合法化提供了帮助。当时被称为西藏嬉皮士的仲巴活佛成功地在西方传播一种心理学化的藏传佛教。这批敏锐的喇嘛将佛教当作唯物主义相对立的精神之学介绍给西方,并将禅修为主的佛教修行方式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手段加以推广。信佛和修佛的目的从脱离轮回变成对心理、精神健康的追求。这样的精神话语(spiritual discourse) 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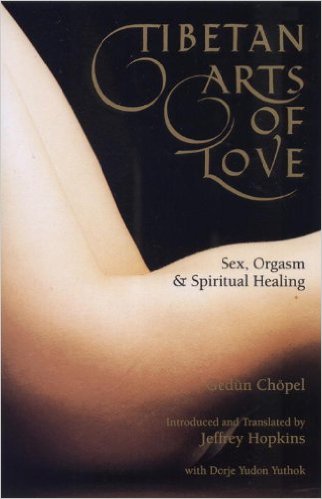
除了神圣化外,西藏和藏传佛教也在西方被不断的情色化。1938年人文主义先驱“疯圣”更敦群培将印度人文主义的经典著作《欲经》改编为《欲论》,后来又被藏传佛教权威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杰佛瑞·霍普金斯(Jeffrey Hopkins)将其翻译成英文,题名为《西藏爱的艺术:性爱、性高潮和精神治疗》(Tibetan Arts of Love: Sex ,Orgasm & Spiritual Healing)改造成为一部修习藏传密教性爱瑜伽的教科书。虽然西藏和内地一样,两性关系并不开放,但并不妨碍西方这种色情化西藏的想象。
沈卫荣认为,西方妖魔化和神话化西藏的历史,反映的实际上是西方的一部心灵史,是一部西方社会文化的变迁史。他们眼中的西藏与现实的西藏无关。今天西方人对西藏的热爱不是对真实西藏的热爱,而是对他们所虚拟的、想象的西藏的热爱。
汉地想象中的“房中术”:对西藏的巫化与色情化
在研究西方想象西藏的过程中,沈卫荣发现,不仅西方对于西藏有东方主义式的误解,实际上汉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西方是完全一样的,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想象”与西方有异曲同工之处。
他指出,1987年初 《人民文学》杂志发表马建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成为文革后第一部禁书。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对西藏色情化,虽然标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但与西藏的现实并不相符,完全是对西藏的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与西方一样都受到了“背景书”的影响 ,是汉文化历史上对西藏想象的翻版。
这种想象最早来自于元末明初的一部题为《庚申外史》的野史。书中记载元朝宫廷中流传的藏传佛教修法有两种,一种是“运气之术”,又称:“演揲儿法”;另外一种是所谓“秘密大喜乐禅定”,又名“多修法”,即藏传密教中的男女双修之法,还提到了一种名为“十六天魔舞”的藏传佛教仪轨。这些野史传说被明初官方史官全盘接受,统统编进《元史》中。于是这段野史,、变成了元末宫廷修习藏传佛教史的官方说法,从此藏传佛教变成了“房中术”、“淫戏”的代名词,甚至成为直接导致元朝不足百年而骤亡的罪魁祸首。

沈卫荣说,今天能够了解到“演揲儿法”和“大喜乐禅定”与色情其实毫无关系。但过去几百年汉族知识分子并不了解它们到底是什么,只能用已有的知识解释。这些汉人想象的故事一直流传下来,自元代以来的汉文文献中,不断出现这些故事的新版本,甚至常常流为色情小说的主题,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见于传为明著名才子唐寅之手的色情小说《僧尼孽海》之中。《僧尼孽海》有一回名“西天僧、西番僧”,即是根据《庚申外史》中有关元朝末宫廷修行“秘密大喜乐法”的故事改编而成的。但其中的具体内容来自汉族之房中经典《素女经》,与藏传密法修行风马牛不相及。除此之外,在晚明的色情小说中多有“番僧”“胡僧”的形象出现。这些都说明代汉族士人对藏传佛教一无所知,必须借助汉族文化中的“背景书”才能对这种属于异文化的东西做出解释。这些内容流传下来直到今天,马原的小说可以说是现代版的《僧尼孽海》,是汉人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想象。
最后沈卫荣指出,汉人对西藏的想象从古代到今天一直在延续,他希望我们对西藏的了解和研究要尽量去除这些想象,还原西藏的真实,不要将自己的愿望和期待投射给西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西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