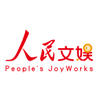“哲学系男神”杨立华,与庄子不期而遇

回顾过往,很多人的人生中都会有一个或者多个决定性的瞬间。
对杨立华来说,其中一个决定性的瞬间发生在1990年。当时,他是浙江大学工程热物理学系一名大二的学生,高等数学的挫败感、乏味枯燥的试验,常常令他闷闷不乐,“想象自己站在工厂里,整个人都是恍惚的,手足无措的”。
课余时间,他读各种书,尤爱文学,曾经梦想过“一边做电厂工程师一边写小说”。偶然一次,他读到蔡志忠的漫画《庄子说》,觉得很有意思,便找来《庄子》的原著,虽没读太懂,却着了迷,“心灵一下子受到触动,感觉进入到一种哲学的状态”,他下定决心:研究中国哲学。

30多年过去,再忆及初遇庄子时的情形,杨立华依然有些唏嘘,“如果不选择中国哲学,或许我将会成为一个读《庄子》而神情绝望的工程师”。
他现在的身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在课堂上讲孔孟、老庄、嵇康、朱子、王阳明等,常常座无虚席,被学生冠以“哲学系男神”。
近日,他将课堂搬到B站,开讲《庄子》,引发热议。
中国文化里的一个巨大漩涡
杨立华在B站讲《庄子》,初衷是读经典。这也是他这些年一直在做的事——1998年北大哲学系博士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每年都带着学生阅读经典,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大家的思想。
“经典之所以经典,就在于它恒常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去读孔子、孟子,其实不是读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哲学家的思考。”杨立华说,经典的阅读要求专深的阅读,可以凝聚精神,把经典转化为当下的思想,并从中汲取持恒的力量。
阅读经典,庄子自然是不可错过的。《庄子》有内篇、外篇、杂篇,共3部7万多字。“我们眼中那个超然的、安贫乐道的、幽默的、汪洋恣肆的、想象诡谲的庄子,大多是故事中的庄子,也就是《庄子》外、杂篇中的庄子。”杨立华说。
在外、杂篇中,杨立华最喜欢的故事源自《庄子·外物》篇:庄子家贫,跑到监河侯家里借钱,监河侯说手头不宽裕,等到年终向百姓征收到税粮再借给他。庄子听后,忿然作色,给监河侯讲了一个故事,说来的路上,听到有声音叫自己,原来是车轱辘印的坑里有水,水里有条鲋鱼,鲋鱼请他弄一瓢水来解渴,他回应说:“你别急,我过两天要到南方去游历,我会引西江之水来救你。”鲋鱼很生气,“等你引来水,我都变成鱼干了”。接着,他对监河侯说,等你收来邑金,你也只能到卖鱼干的地方来找我了。

“这样的庄子真让人迷恋。没有因为自己的贫,而失去对内在自我的确信——他找监河侯借钱,借得理直气壮,借不到还忿然作色。”杨立华说,外、杂篇中有很多这样精彩的故事。
但那些故事,显然不能展现一个真正的、一个作为哲学家的庄子。杨立华认同哲学家钟泰、刘笑敢的考证,认为“内篇是庄子本人所作,外、杂篇有可疑”。基于此,他讲《庄子》,集中在内七篇(包括《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以最庄重的态度深入肌理,直抵庄子哲学思想的核心。
“内七篇里的庄子,是庄子笔下的庄子,跟外、杂篇当中的庄子不是一个庄子。这个庄子是严肃的,也是孤独的。”杨立华说。他讲《庄子》,原因之一就是“读其书,想见其为人”。
多数人读《庄子》,认为惠子是庄子的朋友。“这是一个误解。”惠子是与庄子同时代的哲学家,在《庄子》中多次出场,与庄子辩论,后人常常以为他们是朋友。但杨立华综合了内篇里庄子关于朋友的定义,需要“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友”。庄子和惠子虽有交集,但未达到莫逆于心——他甚至对惠子有过尖锐的嘲讽,“至交好友不会如此”。
此外,庄子还在《大宗师》中借子来这个人物,想象了自己将死时的场景,“妻子环而泣之”,并没有弟子在场。经由种种细节,杨立华得出一个结论:庄子是一个孤独到了极致的人。
杨立华还将内七篇放在一起,分析庄子的写作,“如果庄子今天还活着,绝对是一个伟大的编剧,什么细节都会注意到,基本不会穿帮”。细读文本,他发现庄子喜欢用“十九”这个数字,庖丁解牛那把刀用了十九年;《德充符》里“吾与夫子游十九年”。为何都是十九呢?杨立华猜测,十一年太少,二十年太整齐了,十九年看着像真的,时间又足够久。
“《庄子》最大的魅力在于,无论我们正经历着怎样的生活,在某些时刻我们总会与庄子不期而遇。”杨立华说,而这正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当下性。
比如读《逍遥游》,许多人认为,庄子的思想就是古代版“躺平学”。“但庄子的‘逍遥’并不是指什么都不做。逍遥本身,指向的是对‘用’的消除和挣脱”;讲到《德充符》里的“命”,“《庄子》告诉我们,不确定性或许才是唯一的确定,是生活的真相”;讲《养生主》,“养生”被具体化为“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是个体在世的基本内涵,过此以往,都是额外的负累和添加。从这个角度看,消费主义打造出来的种种充满诱惑力的产品、形象,都成为不必要的多余了”。
“从根本上来说,在表面消极的背后,庄子是有极强的自主和自在的,有自我决定的精神。放在当下,庄子告诉我们可以保持自我,可以对生活中的束缚说‘不’。”杨立华说,进入《庄子》就进入一个无比丰富的思想世界,读得越深,越觉得他是无法穷尽的。也正因为此,“庄子像中国文化里的一个巨大漩涡,所有的人都不同程度地陷入对他的欣赏和迷恋当中。他的思想,在之后激发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家、文人的思考,比如阮籍、陶渊明、苏轼等,也包括鲁迅”。
喧嚣中的固守
对庄子,杨立华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
去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庄子哲学研究》,写下这些年读庄子、研究庄子的所思所想。在书的结尾,他为庄子写下了一个完美的终结:想象中,庄子死于早秋,某个单独的午后。没有病痛。那应该是个晴和的日子,在他最后的世界里,伴随落叶,会有果实坠地的声音。至今,他还记得敲完最后一个字的那个下午,“有一种错觉,两千多年后,终于有人懂你(庄子)了”。

“当然,我也不能完全懂庄子,只能无限接近。偶尔会想:这一生就这样读着《庄子》也是幸福的。有时将它拿到手中,哪怕不翻、不读,也会心安。”杨立华说。每次提及庄子,他的思绪都会回到初遇庄子那一刻,也是他人生道路转折之时。
1991年,遇到《庄子》半年后,杨立华决定考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想拜在陈来门下。陈来师从著名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张岱年。他买了陈来的《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研读,还给陈老师写了一封信,居然收到了回信。后来,他把回信用图钉钉在床对面,每天早上醒来、晚上睡前都看一遍,激励自己。身边的人都不看好他,“我就是觉得自己能考上,很奇怪”。
1992年9月,杨立华到北大哲学系报到,导师正是陈来。

毕竟半路出家,刚入学时压力很大,他下了狠心,天天泡在图书馆,读书、补课。当时,陈来有一门《儒家哲学原著选读》课,在课堂上带着学生读王阳明的《传习录》(下)。“上课读《传习录》(下),那上、中你不读吗?《王阳明全集》都出了,你不读吗?对吧,都要读。” 杨立华说。他性情好静,坐得住冷板凳,又是自己兴趣所在,渐渐入了中国哲学的门。

除了埋头读书,还有青春岁月。当时,杨立华住北大46号楼,室友之间以“子”相称,姜子嗜书、爱买书,杨立华的学问之门“基本上全凭他指点”;裴子笃信佛教,每天必清早起来焚香念佛,因此儒佛之争在寝室里被日常化;还有一位同门,研究北宋心性学的起源。有一段时间,他们在临睡前常背诵陈寅恪的《挽王静安先生》:“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一人一句,极为慷慨。
“现在想来,陈寅恪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意味着喧嚣中的固守。那股狷介之气,至今仍残留在我身上。”杨立华说。
后来,杨立华继续读博,拜在汤一介先生门下。博士还未毕业,他就开始给本科生上课。第一堂《中国哲学史》课,是在1997年冬天的一个下午,讲的是北宋思想家张载,“课程结束时,在那间略显昏暗的教室里,窗外是冬日黄昏的暮色,眼前生动的脸孔上某种被点亮的东西,那一刻也永久地点亮了我。要有怎样的人生,才配得上那一刻的照亮呢?”
收拾精神,自作主宰
杨立华讲课,没有PPT,也不用讲稿。课堂上,他或大段背诵先秦诸子的原文,或用时下流行的词语打趣。他喜欢电影、诗歌、文学,经常将之融入讲解中。
因为幽默风趣,又能将传统经典与现实生活结合,杨立华的哲学课很受欢迎,常常有人来蹭课。课后,还有学生专门梳理他的金句、妙语、段子,发布在网上,流传甚广。比如,“人活着不能太省力,正确的道路一定是用力的方向。”“需要被证明的东西都是不饱满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命’就是不确定,不可测的偶然。”……不少学生都听过他的一则“自嘲式”的趣闻:读博士时,有一次在宿舍做饭,煤油着火,工科出身的他认为不能用水灭火,陷入沉思,邻居手快,端着一盆水,“哗”一下倒上去,火灭了。

“在杨子老师的课堂上,总能被带动起来去反思和感受自身。”曾上过杨立华课的学生佟欣妍回忆说。读本科时,她慕名去“蹭”杨立华的“四书精读”课。有一次临近中秋节,杨立华正好讲孟子,说君子有三乐:一乐家庭平安,二乐心地坦然,三乐教书育人,讲到“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之乐时,情意真切,令人动容。听完这堂课,佟欣妍立马买了车票,回老家和家人一起过中秋。
教学、写作之余,杨立华最大的爱好是下围棋。前围棋国手胡耀宇曾跟随他研读《四书》和《庄子》等经典,久而久之成了好友。胡耀宇常到北大跟他喝咖啡,或课后相聚小酌,偶尔也会下指导棋。近几年,胡耀宇开棋评专栏,杨立华经常拿来读,对围棋有了自己的认知,“围棋之美集中体现为对一切不必要的环节和要素的剪除”。很显然,他的这番理解,融入了中国哲学思考。
“哲学是每个时代最庄严的守护,守护在价值的根基处。”杨立华说,当今这个时代最缺的是沉静的、深入的思考。而思考已成为他的一种习惯——随时随地都在思考,看电影时、读小说时、看球赛时、听音乐时,甚至教育孩子时。也因为此,在家人眼中,他总是心不在焉,和他说话常常驴唇不对马嘴。“在重要的地方,我都要有道理来安顿,不然会心有不安。这就要持续不断地追问和思考,尝试着以思考来面对一切问题。”杨立华说。
研究中国哲学这么多年,杨立华将自己定位为“古代经典世界的一个聆听者”,“尝试着用自己的聆听,去真正触碰那些哲学大家的思想”。他最喜欢南宋哲学家陆九渊讲的“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精神应该把它理解为,由纯一无杂的、单纯的、一致的精神,引申出来的蓬勃的、鼓动的作用”。
读大学时,杨立华就喜欢摇滚、喜欢崔健,这份热爱持续到现在。儿子8岁那年,崔健举办演唱会,他带着儿子一起去看,跟着崔健嚎了一整晚,嗓子都哑了。回家的路上,他一言不发,儿子问:“干吗呢?”他说:“我在想,如果孔子活着,会不会喜欢崔健?”
那天晚上,杨立华想了很久,得出自己的答案:孔子至少不会讨厌——崔健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爆发力,“生命本就应该是饱满洋溢的状态,不能是蔫头耷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