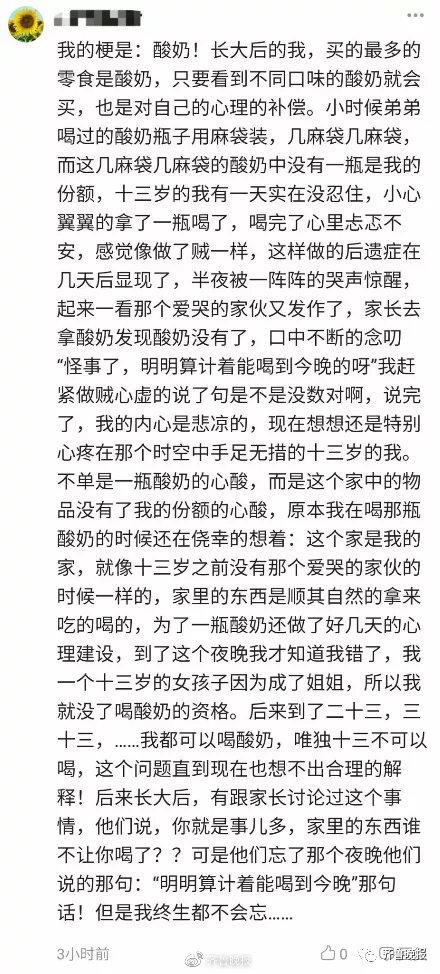如同专为“姐姐”们设置的情感出口,女性题材电影《我的姐姐》的热映,让众多的姐姐从主人公的故事中找到了共鸣。
电影中的姐姐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长大,成长过程中总是被忽视、被打击、被牺牲。父母遭遇意外事故身亡后,留下还在读幼儿园的弟弟。作为姐姐,是承担起亲戚希望“姐姐”承担的责任,还是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姐姐的选择,引发广泛的争议,牵涉出了公众对女性“自我”定义的巨大讨论。
《我的姐姐》在豆瓣上评分7.2,有123101个网友在影评版块留言。12万条留言中,众多女孩们并没有发表影评,而是在介绍自己——当一个女孩成为姐姐,她在生活中的牺牲、退让和收获。

一包麻花
父母又一次在电话中让周琦为即将研究生毕业的弟弟找工作,她终于没忍住发飙了:我也是自己找的工作,他为什么不行?
父母对周琦的愤怒感到莫名其妙:你是姐姐,你工作早,你帮他找工作不应该吗?
从小到大,“你是姐姐,你应该……”是周琦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她和弟弟相差两岁,对于周琦而言,“姐姐”这个称呼,赋予了她无限多的责任:和弟弟争吵时,姐姐必须要让着弟弟;买东西时,姐姐不能跟弟弟争,也不能跟弟弟比;弟弟犯了错,可以原谅,因为还小,但是如果姐姐犯了错,那可能就是一顿打骂,因为“大的带坏了小的”……
周琦理解父母,也对姐姐的身份有了潜移默化的认知:要照顾弟弟,让着弟弟;认可弟弟更重要,因为他是男孩。
“我小时候一直觉得我爸妈其实还好,就是没有特别的偏向。比如说如果有三个苹果,那我爸妈可能会给我弟弟两个,给我一个,所以我还能接受。”
周琦说,察觉到被轻视的源头,是一包麻花。
周琦念初中时,有一天父亲赶集买了包麻花放在了柜子里。
“我以为这么多麻花,我爸会给我一点,让我和弟弟一起吃,但是没有,我爸压根就没有告诉我,只给了我弟弟。”
因为这包没有吃到的麻花,周琦第一次对“姐姐”这个身份产生了质疑:我也是父母的孩子,为什么就一定要处处让着弟弟?
周琦开始在意生活中隐性的不公平:和弟弟读一所高中,弟弟的零用钱永远比自己多;大学毕业后想考研,父母要求周琦“一边工作一边考”,因为“你弟弟还得上学,不能只供你”,但弟弟考研的时候,父母则嘱咐他去报昂贵的考研学习班;工作后买了新手机,父母看到后要求给弟弟也买一个……
作为农村出生的女孩,周琦读完了研究生。虽然师范类大学不收学费,研究生用奖学金也没有花学费,但和身边很多初中没毕业就要出去打工的“姐姐们”相比,周琦已经改写了人生,也正因为如此,父母觉得对周琦可谓“仁至义尽”,并以此为由要求周琦反哺弟弟。弟弟要毕业了,父母要求周琦给弟弟找工作,同时父亲会在有意无意中说,“我们都老了,你弟结婚还得靠你”。每当听到这样的话,周琦都会反驳回去,她反驳的理由是“他是男孩,更要靠自己”,但周琦心里想的理由是“他只是我的弟弟,不是我的儿子,养他是你们的责任。”
周琦从来没跟父母提过梗在她心里的那包麻花,“这实在是一件小事。”她以为会放下,但长大后的周琦,买的最多的零食就是麻花,只要看到不同口味的麻花就会买,“其实我不太爱吃麻花,就是觉得应该补偿自己”。
在父母从小到大的灌输中,弟弟也觉得自己“很重要”。周琦发现,很多时候弟弟将她的照顾和帮助视作理所当然,“因为我是男孩,我很珍贵”。
“有一次我们俩吵架,他说让我滚出去,说这是他的家,以后都是他的。”周琦说到这,笑了一下,
“但是一家人,这些事没办法计较。”
没有选择
电影《我的姐姐》揭示了女性的一个普遍困境,那就是“母亲”、“妻子”、“姐姐”这些身份大于女性自身。一些女性一辈子活在种种身份中,而她们个人的意志、选择、欲望却被剥夺了。
王梅的小名叫“招娣”——作为姐姐,家里希望她能招来一个弟弟,但王梅只“招”来了两个妹妹。第二个妹妹出生后,为了躲避计划生育的罚款,父母把妹妹送了人,并且希望能够继续生出一个弟弟,但是没有成功。
虽然最终家里只有两个女孩,但王梅依然要承担起一个姐姐的责任——王梅比妹妹大三岁,在父母外出躲避计划生育的日子里,妹妹基本都是王梅在照看。作为姐姐,大孩子去照看小孩子,这种情况在王梅身边很普通。她印象里,童年的小伙伴中,当姐姐的身后都会跟着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反之,如果是哥哥,则可以自由地玩耍。因为大人会觉得“男孩子粗心,不会照顾人。”
实际上,在没有选择的成为姐姐之后,“姐姐”就成为了奉献和牺牲的理由。
今年36岁的夏菲是被“牺牲”掉的姐姐。她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在初二下学期交学费的时候,父母说,“你上到初二也能拿初中文凭,省钱让你弟弟妹妹读。”
退学后,和村里的小姐妹一起,夏菲成了深圳电子厂车间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电子厂招工要16岁,夏菲只有15岁,妈妈带着她去找“工头”改大了一岁年龄。组装电子零件是重复动作,日复一日。拿着电焊,在电子板上焊接小小的二极管,拿着电焊的动作有点像拿着笔,但两者又是如此不同——工作时间从早上7点45分到下午5点30,中午休息一个小时。有时遇到着急的订单,加班会到凌晨以后,这种强度令她头昏。

除了工作累,夏菲还想家,向家里人抱怨“太累了”。但在她印象里,大人们只会说,“其他人都能做得到,你怎么就做不到呢?”
在电子厂一个月能挣1000元左右,除了女孩所需要的基本用品,夏菲几乎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了家里。那时候,一年拿回一万块钱,是村里一个打工女孩“合格”的标准。村里的打工女孩们基本都是清一色的“姐姐”,包括夏菲在内,没有人觉得“姐姐”出去打工有什么不妥——既然是姐姐,是老大,就必须要付出,这是姐姐的责任。
打工一年后,夏菲曾经想过重新回来读书——在电子厂,高中毕业的就能当“班长”,大专毕业的就可以不在流水线,工作轻松挣得还多。夏菲计划着,哪怕回来考不上高中,也可以读个职专。跟父母谈起此事之前,她挣扎了很久,在心里预演了很多遍,想在父母面前硬气一点,“毕竟我要回来读书会耽误挣钱。”
据夏菲依回忆,当她提出这个想法后,爸爸问她,“你一年没上学,你还跟得上吗?”夏菲依然表示,“我想读书”,并且举了不同学历在电子厂的待遇和收入,接着爸爸就耷拉了脸:“上什么学早晚都得打工。”
最后,夏菲带了几本初中的课本到了电子厂,准备自学——然而脱离了学校的环境,她缺少自学的毅力,也缺少专业的指导,在外面打工大概4、5年后,夏菲回老家相亲,并很快结婚,有了孩子。丈夫是邻村人,双方知根知底,父母也不允许夏菲在外面谈恋爱远嫁。弟弟妹妹都没有走读书这条路,弟弟参军入伍,妹妹在打了几年工之后也嫁人了。“每年过年,那些在大城市工作的小孩回来后,我爸就感叹我们家没能出一个‘秀才’。”夏菲说,“他用棍子打我弟,我弟都不上学。我想上学,我爸却不让我上。”
“你怨恨父母吗?”
“不恨,那时候太穷了,没办法。”夏菲说,她会让小孩好好读书,“敢不上学我就揍死他。”
一件件的小事
对于一个女孩来说,在自己依然是孩子的时候成为“姐姐”,首先被教育的往往是“姐姐的责任”。
在电影《我的姐姐》影评中,有一条高赞的评论:女孩小时候因为心肌炎治病,用激素药成了一个胖子,而父母则通过孩子的病情向社区申请,获得了生二胎的资格。在孩子大病初愈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迎来了弟弟。
“弟弟出生之后,我原本就不高的家庭地位更加一落千丈。当然了,作为一个懂事的姐姐,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接受,也尽可能站在一个‘七岁大孩子’的立场上去接纳这一切。”
因为爸妈工作忙,奶奶身体不好,所以女孩读大学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弟弟黏在一起,作为姐姐,被教育着学会了任何东西都要先考虑到他,再考虑自己,而这一切女孩一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甚至以为全天下所有的姐姐都和我一样。”
“我花了非常多年,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克服这些大众所谓的‘甜蜜的负担’。我并不恨它,但也请不要逼我一定要去感激它!”
女孩在评论里用了一连串的感叹号,“我认为作为姐姐确实应该要在某些时候负起责任来,但也请不要因此而去绑架所有那些无法负起责任的姐姐们,她们没有错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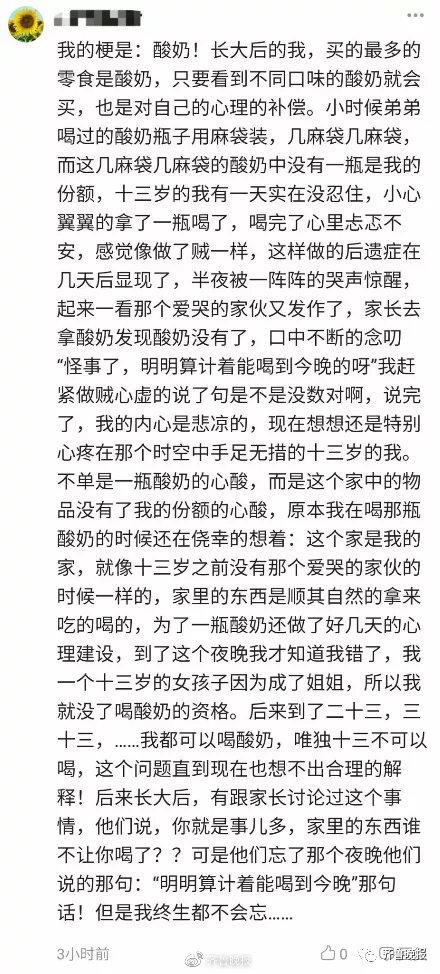
责任,意味着压力,往往也夹杂着委屈。
知乎中有一个高关注度的话题:“作为家里最大的孩子,还是女孩儿,下面有弟弟妹妹,你是什么感觉?”
在网友们举的例子中,很多都是极其微小的事:
父母给了弟弟或者妹妹单独的零食;看电视时永远不能调到自己喜欢的电视台;
要辅导弟弟妹妹的功课,学习下降了会被父母说教;
父母无意中说,“你早晚会嫁出去,我们将来还要靠你弟弟”;
姐弟或者姐妹吵架时,父母拉偏架,一味地要求“姐姐让着”……
1996年,导演李玉曾拍过一部纪录片,取名《姐姐》,讲述了一个小女孩被迫成为姐姐的故事——一对龙凤胎在同一天降生,为了让女孩更好地照顾男孩,父母将女孩确定为姐姐,男孩为弟弟。
有网友对《姐姐》评论:“现实才最残酷,因为你知道那不是演技,而是时时刻刻发生在生活之中。姐姐的委屈与束手无策,妈妈的笑和微妙的表情,爸爸的苦口调解,哦,还有调皮的弟弟,他们太真实。家庭和教育说不清谁对谁错,但这是比生活更沉重的话题。”
让女孩成为自己
采访中,很多姐姐也表达了成为“姐姐”身份的甜蜜:有暖心的弟弟妹妹,是长大之后最大的支撑。
“我们姐弟三个,虽然弟弟最小,但是父母都支持我们读书,尽量一碗水端平。”在家排行老二的王月告诉记者,父母跟大姐一起生活,给大姐看孩子。自己和弟弟目前在外地工作,弟弟现在还没结婚,目前是一家人的“重点打击对象”。
“之前我爸摔到腿,我们姐弟三个轮流伺候着,请了护工基本也没用到,这时候最能感觉到兄弟姐妹的好处。”王月说,他们家的家庭结构是:父母最疼弟弟,但比自己大两岁、性格霸道的大姐在家是绝对的“老大”,自己跟小一岁的弟弟结成“一伙”,反抗大姐的“统治”。
“小时候我大姐确实照顾我们很多,但是我觉得父母做的很好,小时候喝娃哈哈,一板有4个,我们仨一人一个,剩下一个剪子包袱锤,谁赢了谁喝。”王月说,长大工作后,姐弟仨凑钱给没有退休金的父母买了保险,平时父母也不会开口让她们两个姐姐去格外照顾弟弟,“当姐姐的会忍不住主动去多照顾他,也会给他一些钱或者买衣服等,他放假也会给外甥买东西,都是一家人,不用算清楚。”
此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姐姐”,在不公平的家庭环境中争取自己的利益——家里拆迁分到了两套房子,33岁的小丁,在弟弟的反对中争得了自己应得的一套。
“两套房子一套是90多平方,一套是82平方,我弟弟两套都想要,我没同意,跟我爸妈争了很久,最终这套82平方的给了我。”小丁说,父母重男轻女,一直以来,自己都是“要让着弟弟”的姐姐,但是这一次她不想再让着弟弟。
从小到大,为了向父母证明自己是“值得”的孩子,她总是很努力地“听话”,并且考上了大学,而弟弟读书不好,只读到了职专。她毕业后在外地工作,而弟弟一直在老家和父母一起生活,时常需要父母接济。
“父母之所以能够同意把这套小房子给我,一方面是这些年我对家里付出很多,而我弟弟基本都是在索取;另一方面可能是发现我弟靠不住,将来养老还要靠我。”小丁说,因为自己一直以来比较“出息”,父母也渐渐改观了一些重男轻女的看法,尤其是弟弟结婚后生了两个女儿,没有父母一直期盼的孙子,这让父母也“看开了”。小丁说,自己希望将来结婚后能有一个女儿,“我希望她能自由自在,不必成为任何人,不被任何身份束缚,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成为她自己。”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郭春雨
发布于: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