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之前世今生

缘起
1845年7月2日,正在跟画家欧内的妻子莱奥妮·比亚尔幽会的雨果,被愤怒的丈夫和巴黎旺多姆区警察局长逮了个正着。身为贵族院议员,享有豁免权的雨果全身而退。

共和党报纸幸灾乐祸:“一个成功的著名人物被人发现与一名画家的妻子通奸。”
诗人拉马丁在一封信里写道:“我那可怜的朋友雨果的艳事叫我难过,他应当感到痛心的是,在他自由之际还有个可怜的女人正在牢里。”
郁闷的雨果把自己关在屋里,开始书写一个圣人、 一个苦役犯、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女孩的故事。
献给爱女
1843年9月4日,掌上明珠莱奥波尔迪娜不幸溺亡,雨果痛不欲生。
1851年12月11日,雨果以排字工的身份流亡布鲁塞尔;愤怒出诗人,拿破仑三世“这个混蛋只被烤了一面,我要接着烘烤他的另一面”。
1853年9月15日,挚爱亡女的诗人接到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呼唤爱女亡魂的灵动桌,请求他完成《悲惨世界》。
1860年4月26日,雨果打开存放手稿的箱子,继续被1848年二月革命打断的小说创作。
1861年6月30日上午,《悲惨世界》诞生了。
巴黎纸贵
瘦小、活泼的比利时出版商阿尔贝·拉克鲁瓦,以30万法郎(当时价值87公斤黄金)的价码获得《悲惨世界》12年的独家版权。
1862年3月30日,《悲惨世界》第一卷在布鲁塞尔出版,随后又在巴黎、罗马、伦敦、莫斯科出版,“整个巴黎都在迫不急待地读着《悲惨世界》。这部气势博大的作品显示出崇高的情操、凛然的正气,对人类充满怜悯之情,拥有压倒万物的力量,没有谁能够抗拒它的魄力!”
同年5月15日,巴黎帕涅尔出版社首发小说第二卷,比当今好莱坞大片首映还热闹,塞纳街被出版商、记者、送货员、读者挤得水泄不通。拉克鲁瓦几年时间净赚51.7万法郎。
众口难调,任何作品都不可能人见人爱。
拉马丁断定《悲惨世界》“是一本很危险的书,它把最最要命的激情当成无望追求的激情灌输给了读者”;波德莱尔在《林荫道》杂志赞美《悲惨世界》“对人有教育作用,因此是有用的”,私下里却向母亲承认,他“对这部恶劣而荒谬的作品的赞颂之辞实则是一些谎言。我讨厌雨果一家和他的那些学生”。
福楼拜认为“这本书是为信奉天主教社会主义的无耻之徒所写”,名作家巴尔贝·德·奥尔维利报怨书中“不必要的插曲过多,使小说的情节变得支离破碎”。
但,时间证明雨果所言不虚:“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世上还有愚昧和困苦,《悲惨世界》就有其价值。”
影视改编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研制成功具有摄影、放映和洗印等功能的电影机,两年后《悲惨世界》就被搬上了大银幕。其后根据小说改编的50多部影视片,国人最为熟悉的当然是上译厂译制的1958年法、意合拍版。
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很小,只记得冉阿让偷银器被抓,主教以德报怨,从警察手中拯救了冉阿让。

这一无法忘怀的情节,和1981年天津出版的小人书《九三年》,让儿时的我领略了雨果的魅力。

音乐剧《悲惨世界》
1980年9月22日,由阿兰·鲍伯利作词、勋伯格谱曲的《悲惨世界》音乐剧法文版,亮相巴黎体育竞技场。音乐剧沙皇卡梅隆·麦金托什决定将其打造成英文版。5年后,《悲惨世界》英文版在伦敦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雕楼剧院举行盛大首演;1987年3月12日荣登百老汇,成为畅销剧目,风靡世界。
经过长达3年的艰苦谈判,2002年雨果诞辰200周年,《悲惨世界》登陆上海滩:“美国国家巡演团倾情演绎,上海大剧院震撼巨献。”这是该剧在全球第36个国家、第214个城市的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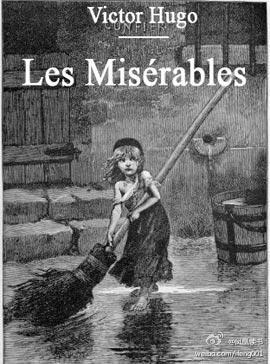
雨果最喜爱的插画家艾米尔·贝阿德制作的小珂赛特,服饰增添中国元素,分外惹人怜爱!

由于故事、人物早已烂熟于心,不懂英语、没看过音乐剧的中国观众,也被大气磅礴、气势恢弘的音乐和精美、华丽的舞台声光效果征服,21场演出口碑爆棚,500元的票价炒至2500。
迄今,《悲惨世界》音乐剧被翻译成21种语言、在全球40多个国家上演、获得近百项大奖(包括托尼奖和格莱美奖),逾6千万人观看了演出。
音乐剧与电影的鸿沟
将这部观众基础雄厚的音乐剧搬上大银幕,如何利用电影的长处,突出音乐剧的特点?

“低头看,低头看!避开他们的眼睛;低头看,低头看!命葬土壑身长埋!”悲愤满怀、铿锵有力的《低头看》,让人想起海涅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我们织,我们织!”

《人民之歌》如《国际歌》一般震撼人心:“民之反暴,奴役必亡 !民之反心,浩浩荡荡!民之战鼓,荡气回肠!民之企盼,历历在望!”
有评论认为,导演汤姆·霍帕“太过忠于音乐剧表演的需要,运用大量的人物脸部特写,放弃了电影在时空剪辑上的优势,使得全片的节奏变得缓慢,叙事压抑沉闷。”
问题在于,若无大量的脸部特写,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是MTV还是音乐剧?
《纽约时报》怨气冲天:“镜头东摇西晃、陡升猛降、满场飞,十分鲁莽。当‘全世界人民’挥舞胜利的法兰西三色旗,观众反而想举白旗:因为你筋疲力尽,终于败给了导演。”
影片获得第85届奥斯卡三项大奖,在中国票房低迷,与其说编导和字幕翻译水平有限,不如说音乐剧作为舞台艺术所特有的形式感与电影追求的真实感之间,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音乐剧直面观众的现场感、雕塑感和舞台空间的神秘感,电影技术再发达也难以完全取代。电影的背景、道具、化妆、表演力求真实,音乐剧的形式美越是璀璨夺目越是容易让电影观众出戏,但让无法亲临现场的观众一解饥渴也是莫大功德。
雨果以厌恶和尊敬的矛盾之情塑造的沙威警长,令人百感交集。
罗素·克劳扮演的沙威狠辣不足,忠厚有余:

法国电视剧版《悲惨世界》(2000),约翰·马尔科维奇出演的沙威气场强大,过目难忘:

自杀场面:音乐剧电影版两手空空的沙威自栏杆上跃下,电视剧版沙威反铐双手,一步步走向深渊。前者貌似忠于原著,实则后者才算领会了雨果的精髓:捉冉阿让是对良心犯罪,放冉阿让是对职责、法律犯罪,沙威自认是罪人,反铐防止自救,也有将罪人铐之以法、面对末日审判的寓意。
不由想起《九三年》:共和军司令郭文情愿被绞死,也要释放良心发现的叛军领袖。
在不同的作品中,以正反两个角色对敌人的捉与放呈现人性的高贵和复杂,雄辩地论证绝对正确的职责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充分体现了雨果的水平。
中国式改编
《悲惨世界》俨然一座宝藏,自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断地被挖掘。影视、动画、连环画、音乐剧、话剧、戏曲,150年过去,《悲惨世界》历经各种语言、艺术形式的翻译、改编,从未停止过探索和争论。
1903年6月,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求新声于异邦”的鲁迅翻译了《芳梯的来历》,以《哀尘》之名发表于《浙江潮》:“此嚣俄(雨果)《随见录》之一,记一贱女子芳梯事者也。芳梯者,《哀史》(《悲惨世界》)中之一人,生而为无心薄命之贱女子也,复不幸举一女,阅尽为母之哀,而辗转苦痛于社会之陷阱者其人也。”
1929年留法归来的李丹、方于结为伉俪,俩人合译的《悲惨世界》第一、二卷,收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一集:“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1977年5月李丹去世,方于独自翻译《悲惨世界》的最后一卷。1984年3月,完整的《悲惨世界》呈现于中国读者面前:

2005年中国戏曲学院庆祝建校55周年,上演京剧版《悲惨世界》:“寒风骤暴雨急,日月昏暗,含屈辱怀怨愤,脱苦海别地狱,整不死的冉阿让,我重返人间!”

恍惚间,“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的杨子荣“重返人间”!
又或是:“昏沉沉,只觉得天旋地转;咬牙关,挺胸站,打不死的吴清华,我还活在人间!”
违和感让网友内牛满面:要是能看到隆美尔在阿拉曼选段里《挑战车》就好了!
话说回来,用雨果酒杯浇自家块垒,又有何不可?
“译者自命豪杰,挥动大笔,对原作宰割挥斥”、“改变原作的主题、结构和人物,或任意增删”的“豪杰译”,在晚清非常流行。苏曼殊译创各半的《悲惨世界》,题名《惨社会》,于1903年10月8日至12月1日在《国民日日报》连载,对原著篡改极多,竟然出现孔二和裹脚,对传统、皇权切齿痛恨。
日益边缘、小众的艺术门类必须保持试验、探索、创造的激情,害怕失败不敢尝试,难免死水一潭。京剧、川剧、越剧、河北梆子版《悲惨世界》,好歹有个动静,怎么也比无人问津强吧。
